但只做絡病學的整理者,顯然不太夠勁。當上醫生后,他開始試著把自己的研究成果,加進方子里。其中一個嘗試,是在一副活血化瘀藥里加入: 8克全蝎。
1982年,一位患者上門復診,開口一句話:“大夫,我吃錯藥了。”
得知這位患者把四次的藥,一口氣全吃了,小吳大夫差點背過氣去。但患者接下來的反映,又讓他大大驚喜: 吃了32克全蝎之后,患者不但沒有異常反應,過去的癥狀也消失了。
這一年的年底,吳以嶺發明了一款新藥:五龍丹。除了全蝎,另外四龍分別是: 水蛭、土鱉蟲、蜈蚣、蟬蛻。
這款新藥,還有一個別名: 通心絡。
1985年,“中藥通心絡治療冠心病研究”被列為河北“省科委攻關項目”,并下撥5000元科研經費,進行動物實驗。
但面對臨床研究,5000元的經費顯然不夠,吳以嶺只好自掏6萬元,聯系石家莊中藥廠,協助制備了300人份的觀察藥品。
1988年,吳以嶺的“偏方”終于轉正,獲得了臨床研究的認可,背了一身債的吳以嶺,第一次從新藥里看到了產業化的商機。
作為一位很抹得開“知識分子”面子的創業者,吳以嶺先后敲了十幾家制藥企業的門,均被拒絕。絕望之際,石家莊高新技術開發區伸出了手,希望他能讓通心絡留在河北、留在石家莊。
1992年1月29日,辭掉“鐵飯碗”的吳以嶺,走進石家莊高新技術開發區,遞交了開辦醫藥研究所的申請。并于6月16日正式開業,這就是以嶺藥業的前身。
有了開發區許諾的支持,吳以嶺的“雄心”倍增。他馬上遞交了計劃申請書,省、市、開發區的領導給予了最大支持,7天就批準了制藥企業的建設規劃。
自此,吳以嶺一邊招兵買馬,一邊加緊新藥研發。通心絡膠囊的審批,也像是上了“高速公路”,1995年10月份上報衛生部,1996年8月就拿到了國家級新藥證書和生產批號。
萬事俱備,通心絡開始“攻城掠地”。
1997年,吳以嶺親任公司銷售部經理,為了讓銷售軍團更有戰斗力,公司所有業務代表至少是大專以上學歷,各大地區經理均有醫學學士或醫學碩士學位。并在北京、上海、長沙等26個省市設立了銷售辦事處,銷售網絡擴展到全國。
通心絡項目的確沒有辜負吳以嶺的期望: 先是獲河北省衛生廳科技進步一等獎,又于1997年榮獲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進步二等獎等榮譽。
吳以嶺采用學術品牌推動戰術營銷的模式,借勢放大產品知名度。1999年,遠近聞名的通心絡迎來了2000多家經銷商,并一舉闖進全國500多家醫院和藥房。進入高速擴張期的通心絡,四年間銷售額就突破5億元。

如今,每年使用通心絡膠囊的患者上千萬。靠著“五只蟲子”,吳以嶺挖到了他的“第一桶金”。
【神藥來了】
2002年底,廣東民間出現了一種致命怪病的傳言,一時間人心惶惶。接著,就發生了搶購米醋和板藍根的風潮。平時不到10元一大包的板藍根一下翻三倍,甚至有記者拍到1000元一瓶白醋。
這種怪病,正是被稱為“非典”的SARS病毒。
2003年3月6日,北京接報第一例輸入性非典病例。參加完兩會后,身為全國政協委員的吳以嶺立即趕回公司,成立針對SARS病毒的中藥科研組。
在這背后,吳以嶺對非典的病理學看法,其實來自于傳統中醫的“瘟疫”范疇,它因“疫毒”而發,因此也具有疫毒所致疾病“起病急、傳變快、表證短暫、較快出現高熱、煩渴”的主要臨床表現。
這似乎與“非典”起病即高熱、寒戰、肌痛、干咳的主要癥狀基本一致。
據此,吳以嶺提出了一個宣肺泄熱的配方,采用連翹、金銀花、炙麻黃、炒苦杏仁、石膏、板藍根、綿馬貫眾、魚腥草、廣藿香、大黃、紅景天、薄荷腦、甘草等藥物清瘟解毒。
但在經歷347天的研發工作后,連花清瘟卻因為非典的終結,成了一個晚到的“來客”,面臨著尷尬和落寞。直到2008年,以嶺藥業以通心絡為代表的心腦血管類藥物銷售額達8.47億元,營收占比91.08%,連花清瘟卻不到6500萬元。
但連花清瘟的“時運”,只是遲來了些。
2009年,在甲型H1N1流感的恐慌陰霾里,連花清瘟卻找到了“大展拳腳”的機會。
8月21日,在衛生部、世界衛生組織和《柳葉刀》雜志共同舉辦的流感大流行研討會上,以嶺藥業宣布了連花清瘟膠囊的重大突破消息:
“北京地壇醫院中西醫結合中心選取66例甲型H1N1流感患者,分別使用連花清瘟與更知名的西藥抗病毒藥物達菲,進行隨機臨床試驗。結果顯示,連花清瘟膠囊組病毒核酸陰轉時間與治療效果,顯著優于達菲。且其費用低廉,成本僅為達菲的八分之一。”
“連花清瘟膠囊防治流感效果超過達菲”的消息,第一時間被上百家權威媒體報道。8月29日,連花清瘟抗流感新聞,還出現在中央電視臺《新聞聯播》。
在2009年衛生部《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診療方案》里,雙黃連、藿香正氣等與連花清瘟一起列入其中。但市場的“寵兒”,最終只有一個。
默默無聞的連花清瘟,其城市人群品牌知曉率迅速躍升到80%,銷售額更是增長近6.7倍,突破5億元。
嘗到甜頭的以嶺藥業,似乎看到了一個冉冉升起的“新星”。2010年,以嶺藥業大張旗鼓地找來張國立作明星代言人,并積極投放市場廣告。
但它在批準的“廣譜抗病毒”之外增加了抑制禽流感、SARS等說法,被廣東、上海、江蘇、安徽等省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,視為夸大產品功能主治、利用醫藥科研名義做證明,成為“未經審批,虛假宣傳”的嚴重違規案例。
隨著流感疫情逐漸消退,連花清瘟的銷量又低迷到7500萬元左右。
沉寂兩年后,一場普通的科研成果發布會,讓連花清瘟又一次找到了“舞臺”。

2012年9月13日成都召開的“第十三次全國呼吸病學學術會議”上,以嶺藥業宣稱“連花清瘟膠囊有明確的抗菌作用”,并拋出“十二五期末(2015年)達到10億元銷售額”計劃。
9月14日,一篇《連花清瘟抗菌研究獲突破,以嶺藥業將笑傲限抗時代》的文章,將上市的以嶺藥業推到“鎂光燈”下。鑒于消息重大且從未披露,以嶺藥業當天被深交所臨時停牌。
原來,被稱為史上最嚴“限抗令”的辦法于8月1日正式實施。醫生對普通感冒不能隨便開抗生素藥,如果作為中成藥替代品的連花清瘟,被證實具有“抗菌”作用,無疑有利于擴張以嶺藥業薄弱的醫院渠道。
如此蹭熱點,被媒體直斥為“以嶺藥業另類炒作法”。
不過,以嶺藥業顯然不想再“看天吃飯”,它錨定了感冒或流感用藥市場。開始大規模招聘針對醫院的銷售人員,且絕不愿錯過任何一場“健康危機”營銷。
2013年初,新浪微博上排名首位的話題是“求霧散”,霧霾成為新的“健康話題”。3月以嶺藥業的2012年度報告中,就提到對霧霾顆粒主要組成的汽車尾氣,引起的“實驗動物肺部炎癥損傷具有良好保護作用”。
2013年年度報告里,以嶺藥業又直言:“連花清瘟產品及時抓住了一月份的甲流和四月份的禽流感兩次機會,并以此為契機增加其覆蓋率與知名度,增速同比超過60%。”
此后,連花清瘟份額穩步上升,并于2015年成為全國前三強,銷售額也恢復到5億以上。
2018年,最嚴重的一次流感襲來。國家衛健委數據顯示,僅1月和2月的流感死亡數,就遠超前兩年之和。
成為國家衛計委《流行性感冒診療方案(2018年版)》里,13種中成藥推薦之一的連花清瘟,再次復刻2009年的“爆發奇跡”,一季度銷售額就追上去年全年。
這一年,連花清瘟在中成藥感冒用藥銷售收入排名位列第1名,突破10億元大關。相比于競爭力長期低迷的通心絡膠囊,誕生15年的連花清瘟,終于成為以嶺藥業的“新王牌”。
2020年疫情爆發,為已登頂的連花清瘟走上“神壇”,加了最后一把火。三年來,其出廠銷售額已達百億元之巨。
過去兩個多月,以嶺藥業市值一度暴漲至最高超800億元,吳以嶺身家也因此暴增至238億成中國“最富院士”。
一路封神的連花清瘟,正如一篇文章提到, “沒有錯失任何一次災難背后的機會”。
【院士與首富】
吳以嶺身上的“光環”極多,名中醫、政協委員、河北石家莊首富……更被外界稱贊“做企業做到上市,做學問做到院士”。
既是“院士企業家”,也是中醫院士,是其最引人注目的稀缺“光環”。而這,與吳以嶺的中醫學術之路分不開。
絡病理論在中醫學術理論體系里,淵源悠久。第一部中醫理論著作《黃帝內經》中,就提出了經絡學說,其對心腦血管病、腫瘤、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治療,具有獨特價值。
二千多年來,學術傳統一直“重經脈輕絡脈”。清代醫家喻嘉言遺憾地說:“十二經脈,前賢論之詳矣,而絡脈則未之及,亦缺典也”,即沒有系統的絡脈學說面世。
這給了吳以嶺著書立說的“市場”,在河北中醫院做心血管內科醫生時,他就結合臨床實踐創建了絡病臨床辨證論治體系——絡病證治,并創立了脈絡學說。
通心絡膠囊的誕生,正是源于這一學說。2000年2月19日,“通心絡膠囊治療冠心病的研究”,因在國內首創運用絡病理論的重大理論創新,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。
臨床應用的成功,讓吳以嶺的絡病學研究進入“爆發”階段。
2004年,185萬字篇幅的《絡病學》出版。該書還作為教材,在國內40余家高等醫學院校及新加坡中醫學院開課。這讓吳以嶺,成為中醫絡病學的體系創立者和學科帶頭人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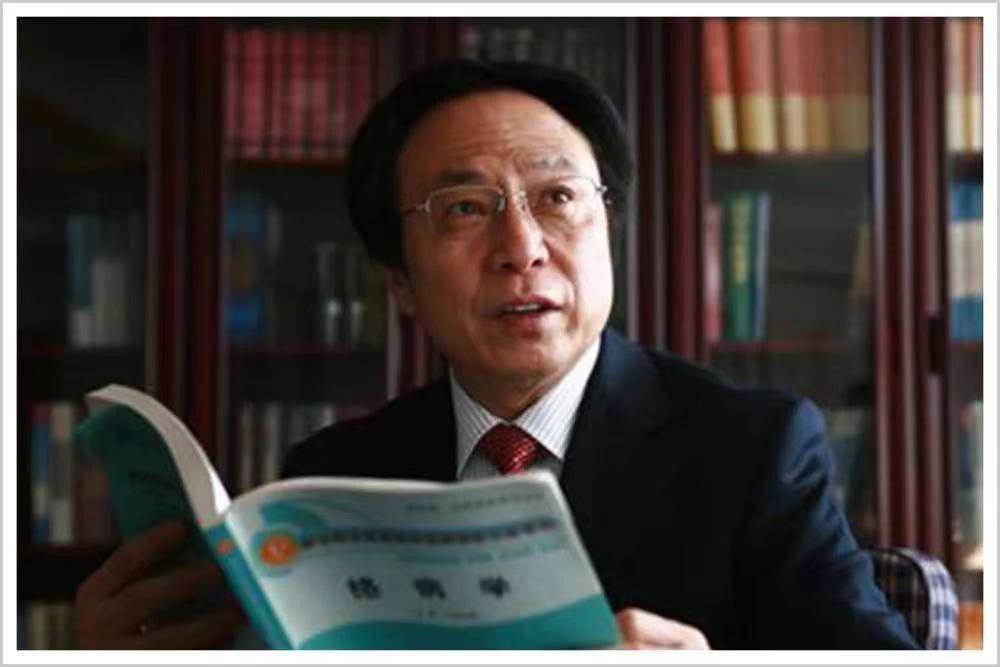
2005年7月1日,國家科技部將“絡病理論指導血管病變基礎研究”,確定為最高級別的973項目,吳以嶺成為河北省首位973項目首席科學家。2007年2月27日,其“絡病理論及其應用研究”項目,再次獲得2006年度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。
2007年,榮譽滿滿的吳以嶺沖擊中國工程院“院士”頭銜,并進入第二輪評審,但最終未果。
直到2009年,爆火的連花清瘟不僅在三年后,榮獲2011年度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。并助推吳以嶺,當選“2009中醫藥發展最具影響力新聞人物”。
也是這一年年末,吳以嶺成功當選院士。這為以嶺藥業研發上的“院士朋友圈”,打開了閥門。
公開信息顯示,2012年掛牌的以嶺藥業石家莊生物醫藥院士工作站,三年間就有了樊代明、鐘南山、張伯禮等20余位兩院生物醫藥領域院士簽約入站,建立院士專家委員會。
其中,用于冠心病的芪藶強心膠囊的臨床研究,就是與阜外醫院高潤霖院士、天津中醫藥大學張伯禮院士合作完成。2015年,則與鐘南山院士帶領的廣州呼吸病研究所,簽訂有關連花清瘟系列產品的研究戰略合作項目。
一位中醫藥行業人士在采訪時感嘆到,以嶺藥業那棟“院士樓”令人印象深刻:“不僅僅是中藥領域的,中國還有哪家藥企能有這么強大的‘院士團隊’?”
外界曾質疑吳以嶺搞“學術圈裙帶關系”,對于這一點,吳以嶺似乎不曾做過正面回應,他反而更喜歡對外宣稱自己的務實精神:
“學術創新不能光停留在紙上,要實際解決臨床看病的問題。”
在一定程度上,以嶺藥業確實努力在生產設備與工藝上投入。早在2003年,以嶺藥業就建立了世界一流的新藥評價中心,是河北省第一家國家GLP認證實驗室。
2006年,以嶺藥業采用了投入1億多元、和清華大學聯合攻關5年的科研成果——蟲類藥超微粉碎技術。解決了現代中藥生產研發中,用最小服用劑量取得最大藥效的課題,并節約近1/3生產原材料。
循證醫學,是目前世界最權威的藥物療效研究方法之一。2008年,以嶺藥業參松養心膠囊完成了由30多家三級甲等醫院參與的“抗心律失常循證醫學研究”,是我國該領域第一個開展此研究的中藥。
但是,以嶺藥業沒能避免國內藥企“重營銷輕研發”的通病。
公司年報顯示,2021年以嶺藥業研發投入8.38億元,占營業收入比重8.28%,研發營收比連年增長。在中藥上市企業中,處于第一梯隊。
但真正的大頭,還是銷售費用。2019-2021年,以嶺藥業銷售費用分別為22.27億元、30.35億元、34.34億元,平均占比35%左右。
主要原因是,以嶺藥業將以學術會議在內的“學術推廣”,作為撬動業績的重要手段。并且,公司通過占比六成高達9095人的銷售人員,建立了覆蓋全國的學術營銷推廣網絡,并鏈接10萬余家醫療終端,30萬余家藥店終端。
這甚至直接影響了公司利潤水平,近五年以嶺藥業產品綜合毛利率穩居在65%左右,高于行業平均水平。但同時,以嶺藥業的凈利率卻始終在10%-15%徘徊,呈現出增收不增利的窘況。
從第一桶金的“五只蟲子”,到走上神壇的連花清瘟。吳以嶺與其以嶺藥業,成于學術、盛于營銷,以中國制藥行業的現狀來看,這似乎已經是業界的通例,并沒有太多可詬病之處。
在2019年的“中西醫結合血管病學大會”上,在吳以嶺做完報告后,湖北省中醫藥學會會長王華教授做了個點評:
“吳以嶺院士傳承張仲景之醫道,弘揚李時珍之精神,為我國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,是當代中醫人的楷模。”
王華教授的點評,吳以嶺院士想必會很滿意,但張仲景和李時珍是不是也這么想?
【參考資料】
[1]《從通心絡25年的發展看科學家吳以嶺的成長》人物
[2]《連花清瘟之父:靠幾條蟲子每月1.5億利潤,出診費八年多不改》漂江孤影
[3]《吳以嶺:不忘初心,執著中醫》環球飛行
——END——
歡迎關注【華商韜略】,識風云人物,讀韜略傳奇。
版權所有,禁止私自轉載
部分圖片來源于網絡
如涉及侵權,請聯系刪除
責任編輯: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