節度使制度正式確立于唐玄宗開元年間,這一時期節度使在數量和職權方面均有所發展。截止到天寶元年,唐廷于東北和西北邊境地區一共設置了十個節度、經略使,分別為安西節度使、北庭節度使、河西節度使、朔方節度使、河東節度使、范陽節度使、平盧節度使、陳右節度使、劍南節度使以及在嶺南地區設置的嶺南五府經略使。同時,節度使的權力也不斷擴張,兼任采訪使,史載:“初,節度與采訪各置一人,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”釆訪使作為“道”的監察長官,類似于西漢時期的“刺史”,處于由監察官員向地方長官的過度階段。不久,節度使皆行采訪使之職權,“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,后改為采訪處置使,治於所部之大郡。既又改為觀察,其有戎旅之地,即置節度使”這樣節度使就間接獲得了掌管州縣地方事務的權力。在玄宗時期,使職差遣化日益嚴重,節度使往往還獲得其它方面的使職。如開元二十八年,安祿山就有以下頭銜,除了持節充平盧節度使外,還兼度支、營田、陸運、捍(押)兩蕃、激海、黑水等四府經略、處置、平盧軍攝御史大夫、管內采訪處置使等,其中“支度使”掌管地方的財政,“營田使”則掌管地方的營田和屯田。可見,幵元、天寶年間,節度使已經逐步掌控了地方的軍權、政權、財權,就是所謂的“既有其土地,又有其人民,又有其甲兵,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”。在節度使制度下,中央權力下移,于是“方鎮不得不強,京師不得不弱,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,以此也”。此時,節度使的職權已經基本具備,唐代中后期的節度使制度已經基本形成了。玄宗時期節度使制度的特點。
天寶元年,唐王朝形成了“十節度、經略使”邊疆格局。與唐代中期相比,玄宗時期的節度使制度,有以下特點:
節度使只于延邊地區設置,執行防御外族入侵的職能。玄宗時期節度使主要為了應對當時的邊境戰爭,是出于邊防的要求而設置的,“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、堅昆……河西節度斷隔吐蕃、突厥……朔方節度捍御突厥……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御突厥……范陽節度臨制奚、契丹……平盧節度鎮撫室韋、秣鞮……隗右節度備御吐蕃……劍南節度西抗吐蕃,南撫蠻猿……嶺南五府經略緩靖夷、猿”,此時的節度、經略使的轄區只局限于邊地,主要掌管邊地的軍事事務。由于李林甫為阻絕節度使“出將入相”之路,建議玄宗大量任用胡人,因此天寶之后的節度使也大多由能征慣戰的胡人擔任,如安祿山、安思順、哥舒翰、高仙芝等皆為外族,這盡管有利于削弱節度使對內地事務的影響,也有利于唐廷對節度使的控制,但也容易使其產生獨立傾向。

此時的節度使尚不具備割據的條件。此時的十大節度、經略使己經擁有地方的行政、財政、軍權,但是并不具備割據的可能,“節度使既是適應邊境軍事需要而設,統率軍鎮、指揮軍事活動自然是他們的主要權力。史料顯示,開元天寶時期,無論是指揮戰爭的重大決策,還是設置軍鎮、備邊、募兵等措置,節度使都要上奏朝廷,遵循中央的旨意行事,并沒有專擅之權”。節度、經略使擁有一部分財權,但是“凡天下邊軍,皆有支度之使,以計軍資、糧仗之用。每歲所費,皆申度支而會計之,以《長行旨》為準。支度使及軍州,每年終,各具破用、見在數,申金部、度支、倉部勘會”沒有獨立的財權,節度使就也無法實現地方的軍事割據。
開元時期募兵制改革的完成,天寶元年“十節度、經略使”邊疆格局的形成,幾乎是同一個過程。掌控地方眾多職權的節度使擁有募兵之權,就將募兵制和節度使制度結合起來,這標志著藩鎮體制的形成。藩鎮體制對玄宗朝的政治和軍事有深遠的影響,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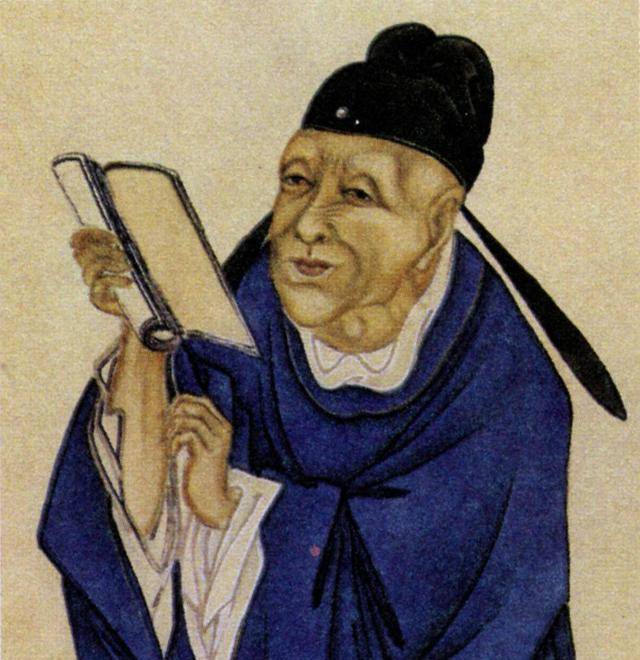
首先,藩鎮體制破壞了唐王朝傳統府兵制下的“內重外輕”軍事格局,變成了“外重內輕”。天寶元年,唐王朝的軍隊總數為人,其中藩鎮控制的兵力就達到人,占到總數,占絕對的優勢。唐廷雖然建立了“擴騎”,但是兵力有限,也沒有得到唐廷應有的重視,于是強兵猛將多集中于邊疆,內地兵力空虛。
其次,節度使集軍、政、財大權于一身,而且不僅控制一鎮,還出現一人兼領數鎮的現象,如“因(王)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,判武威郡事,充河西、陳右節度使。其月,又權知朔方、河東節度使事。忠嗣佩四將印,控制萬里,勁兵重鎮,皆歸掌握,自國初已來,未之有也”這樣節度使就變成獨霸數鎮的“軍閥”。
再次,節度使任期太長,這就為其專擅提供了條件。唐玄宗邊疆戰爭頻繁,但是良將難尋,于是一些將領久任不替,史載:“自唐興以來,邊帥皆用忠厚名臣,不久任,不遙領,不兼統,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。其四夷之將,雖才略如

阿史那社爾、契甚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,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。及開元中,天子有吞四夷之志,為邊將者十馀年不易,始久任矣”,如安祿山出任平盧節度使長達十五年,兼任范陽節度使又十二年,兼河東節度使也達到五年之久。這種情況下,節度使培植黨羽的可能性大為增加,地方將士“唯知其將之恩威,而不知有天子”,增加了地方軍事割據的可能性。
責任編輯:




